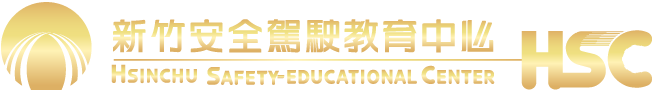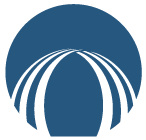中國時報【何國雄】
她坐在石頭邊笑得謎樣,隨興赤足用腳滑起水來,一會兒又唱起民歌,甜美的歌聲繚繞山谷,我點了首她最愛的〈野薑花的回憶〉:「三月裡,微風輕吹,吹過漫山遍野……」一時之間,感覺整座山谷都飄滿野薑花淡淡的芬芳。
為了把心裡的話說完,暑假時,我開車北上宜蘭。
雪隧過後,心情就莫名亢奮起來,遠遠的龜山島在天朗氣清的三月初,龜的頭清晰可見。同行的人說,龜山島會隨著潮汐而划水,一旁的我笑說,那僅是角度的錯覺。隨著車行,不同時間看了一下島龜,似乎那龜真的游了起來。是真的耶!那是隻會游泳的島,我幾乎快叫了出來!
島龜和二高之間的海岸線前是一大幅宜蘭平原,寬闊平坦得像是用丁字尺作圖似的,錯落的村莊旁邊還可以看見一畦一畦的農田,溝渠旁的透天厝,種滿一大片野薑花,遠遠望去,冒出頭的白花,像一隻隻靜止的蝶,我以為那裡就是她的家。
理所當然的初戀
那年,她幾次跟我說,有空可以到她們「宜蘭羅東」來玩。我遲遲沒有允諾,倒是常常下課了,入了夜,我們一群人窩在苗栗山上的空教室裡唱起民歌。那時,大學城創作歌謠比賽已經停辦了幾年,說是民歌時代的末流也不為過,流行樂和搖滾風開始正式大量入侵民歌,我們正值十八、九歲,甫上二專一年級,我們幾個新鮮人用一把尼龍弦吉他對抗卡拉ok,也用僅會的四大和弦唱出我們能想得出來的歌。
唱歌之餘,她常常是不發一語的;唱歌的時候,她也只是跟著大家唱。同學間,湘姊長我們四五歲,她常常主音一開口,其餘的女同學就會跟著和起歌來,湘姊懂得歌很多,她說自己以前是教會唱詩班的,第一次聽湘姊唱歌的人,通常會出乎意料的起雞皮疙瘩。她是偎在湘姊旁的幾個女孩子中的一個,身上總是一襲素白洋裝。
有一次,我抓起吉他胡亂彈起弦來,她偷偷在我身旁說:「你也會彈?」很驚訝似的!我沒有回答她的話,只是靜靜地笑,她也跟著笑,那一次我發現她是一位單眼皮的女孩。
科系新生盃籃球賽的時候,她跟著湘姊在人群中幫男同學加油。像我們這種遊走在藝術與工程邊緣的陶業科,比起陽剛味濃烈的工程科,場上總是輸多贏少。高中打過HBL第一級的我,常常成了科內悲劇英雄,當然偶爾也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。但不管場上緊張刺激與否,她的表情永遠淡然,並不會有太多的裝飾情緒在她的清湯掛麵上。她會在我休息的時候為我遞上乾毛巾,有時直接給我口茶喝;我也會習慣把一些重要證件放在她那兒保管,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就是初戀,覺得一切理所當然。
時隔25年的宜蘭
遇連續假期的時候,她常會問要不要跟她回宜蘭玩?我總是笑著說,下次吧!說完,常見到她失落的眼角似乎泛起淚光,我安慰著她說,將來一有機會,我一定會去宜蘭找她。真的。
我是真的來找她了,不過,時隔二十五年。
回頭,那隻島龜已經游離我們身後,像我和她二十五年的距離。下了高速公路後,除了可以感覺到宜蘭在地的農村樣貌外,還有讓人嘖嘖稱奇的豪華民宿。我與同行友人在驚呼中開足了眼界,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,瞠目結舌。其實我遊遍各地,美麗雄偉的建築倒也看過不少,但是宜蘭這裡,五步一民宿、十步一豪宅的特殊景觀,台灣寶島也算少有。例行地,同行之人總會說,將來如果退休的話可以來這裡買地養老,或者說來這兒開民宿等等之類的話!像這些嘴角願望聽聽就好,我並不搭腔,倒是認真思考來宜蘭定居的問題,想起了她以前很喜歡問我要不要跟她回宜蘭玩的事。
聽說,她嫁人之後就回宜蘭定居了,像遠去的風箏,飄在很遠的地方。
我撥了通很久很久以前她留給我的家電,電話那頭說姑姑已經沒有住在那兒了。年輕的男聲客氣地要我留下名字和聯絡電話,他說他會幫我代為轉達,順口問了我是誰?一時之間,我吃了螺絲似的說不出話來。後來,我匆匆留下了手機號碼和姓名,又說會在宜蘭待上三天,請他「務必」轉達她口中的「姑姑」,因為,我有一些話想當面跟她說。自那一刻起,我像得了強迫症,有意無意地就拿出手機看了看。三天中,無聲無息。第四天過後,我知道,她不會打來了。
與世界短暫隔離
那年,手機還未問世,BB call正要流行,所以只要一離開群體或是私奔,隨時可以與世界脫節。某日窮極無聊的實驗課,她低頭塗鴉,我丟了張紙條問她願不願意立刻跟我回台中?她看著我,用唇語說「蹺課!」我微笑點頭。於是胡亂收拾一下,便挽著她的手從實驗室後頭溜走,踉蹌追上開往台中的巴士,帶著她與世界短暫隔絕。我們去山上抓溪蝦,從三點到五點,整整抓了幾百隻。她坐在石頭邊笑得謎樣,隨興赤足用腳划起水來,一會兒又唱起民歌,甜美的歌聲繚繞山谷,我點了首她最愛的〈野薑花的回憶〉:「三月裡,微風輕吹,吹過漫山遍野……」一時之間,感覺整座山谷都飄滿野薑花淡淡的芬芳。我用雙手做擴音機般朝著她大聲說,我以後要娶她,她笑著叫我別發神經了。
二專畢業後,我去當兵了。懇親會的時候她來看我,她的話不多,多數時間她只是笑,像在籃球場上看我打球那樣,僅露出幾顆白皙的潔牙。離去的時候她說,她待在台中的一間陶藝教室當助教,教幼稚園小朋友捏陶樂,她說她喜歡小朋友,也想當一位真正的老師,可是當時我們都只有專科的學歷,距離當老師至少還有兩步路。我放假後去看了她幾次,她又跟我說她也羨慕軍旅生涯,過沒多久,就聽說她去投考女青年工作大隊,當起女軍官來。她的姊妹淘都很難理解她的決定,我也很意外,但是我不問她原因,我知道她有自己的想法。
下部隊的她開始在全國各營區勞軍,我那時已經退伍了,隔年以吊車尾之姿插班進東海中文系。有一次,她說她在台南官田新訓中心,星期三放軍官散步假,問我要不要去看她。那天,我一告別杜甫詩,就直奔台南,我們在火車站前見了面,她穿起軍服神采奕奕,我站在人群裡大聲說:「教官好!」她笑了,又叫我別發神經,我說我沒有;又說,以後當上正式老師的時候要娶她,她又笑了,輕輕捶了我一下。我們吃了飯,聊了一些話,她多半靜靜的聽著我說大學生活裡的點滴。因為必須趕在十點前送她回去,匆忙之中,我說,來不及的話等下次再說。送完她回國軍英雄館的時候,我趕上最後一班自強號回台中,才一上火車,思念像長了根似的蔓延。
(上)